(記者 楊銳冰 張晶晶/文 牟進勇 樊曉姝/圖)父親早逝,她立志研制“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藥”,來自南城街道九齡社區的鄭惠文今年572分考取南京中醫藥大學;在灌南縣李集鎮久安村的一家小店里,患小兒麻痹癥導致腿腳不便的父親守著微薄生計,18歲的劉文文以582分的高考成績考入揚州大學;父母在他不到1歲時離異,父親輾轉工地打工,畢業于灌南高級中學的嚴蘇宇今年546分考取江蘇理工大學;三間瓦房靜立在玉米地旁,68歲的父親周良崗忍著病痛割凈門前雜草,屋內霉味隱約,剛考上重慶師范大學專升本的周小洲站在為5000元本科學費徹夜難眠……
這是四個用讀書劈開荊棘的故事,更是四盞在泥濘中依然灼灼燃燒的星火。
父親早逝,她立志研制“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藥”
鄭惠文572分考取南京中醫藥大學

深夜,當同學們早已進入夢鄉,17歲的鄭惠文還在昏黃的臺燈下啃著物理題。草稿紙堆了半尺高,額頭上沁出細密的汗珠。“只要多學一點,離夢想就更近一點。”
10歲那年,父親因病去世。那時候,小小的鄭惠文就萌生學醫藥的念頭。7年后,這個念頭長成了參天大樹。今年高考,鄭惠文以572分的成績被南京中醫藥大學生物制藥專業錄取。她選擇這條路的理由簡單而沉重:“我想研究出價格更親民的特效藥,不讓更多家庭經歷我家的痛苦。”

推開位于南城街道九齡社區鄭惠文家的門,撲面而來的是生活的重壓與不屈的生機。79歲的爺爺和76歲的奶奶年邁無勞動能力,母親楊利是全家唯一的支柱,做著保潔工作,每月收入僅2000余元。這個七口之家,有五人吃著低保,每月2000多元的低保金是重要的補充。除去四個都在上學的孩子——讀初中的妹妹和讀小學的雙胞胎弟弟——學費生活費壓得這個家捉襟見肘。
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”,鄭惠文早早體味了這句話的滋味。父親去世后,她瞬間長大,學習之余的所有精力都用來幫母親分擔。這個暑假,當同齡人憧憬著難得的放松,她卻忙著做家教,一站就是幾個小時。她不僅為自己積攢大學學費,還主動擔起為弟弟妹妹輔導功課的責任。“姐姐就像我們的小老師,”妹妹說,“但她對自己最嚴格。”
 ?
?
生活的風霜從未磨滅她眼底的光,反而鑄就了她超乎常人的韌性與清醒。談到學習,鄭惠文沒有太多“竅門”,她的經驗樸實得讓人動容:“就是多跟著老師的節奏,然后拼命找自己的不足。”高中物理曾是她最大的“攔路虎”,成績一度在三四十分間徘徊。換作他人,或許早已放棄,
但她偏不。
無數個夜晚,家里那盞舊臺燈總是亮到很晚。她埋頭于一道道令人頭疼的物理題,網上查找資料、反復觀看教學視頻、自學消化。演算的草稿紙堆起半尺高,額頭上常因專注而沁出細密的汗珠。“那時候就想,我不能輸,我得多學一點,再學一點……”回憶往昔,她語氣平靜。
最終,她的物理成績在高考時突破了70分。這30分的躍升,背后是無數個夜晚的孤燈奮戰,是一個寒門學子“知識改變命運”的堅定信仰。
她清楚地知道,這條路很長,本科僅僅是個起點,“我今后還要繼續讀研。”深入科研領域,去真正觸碰那個“研制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藥”的夢想。鄭惠文用她的故事告訴世人:生命予你以苦難,你卻報之以歌,用堅韌作譜,以奮斗為詞,終能響徹云霄。她不僅為自己掙來了一張掙脫困境的門票,更矢志為無數像她曾經一樣無助的家庭,點燃一束科學帶來的、充滿溫度的希望之光。
殘疾父親開小店托舉夢想
劉文文582分考取揚州大學

在灌南縣李集鎮久安村的鄉間小路上,一間沒有招牌的鄉村小店藏在綠樹掩映中。門口斑駁的墻面上,“劉金全商店”幾個紅色油漆字是它唯一的標識——這里售賣著煙、水和飲料,顧客多是本村鄉鄰,生意清淡得幾乎不掙錢,卻是劉金全和兒子劉文文相依為命的“根據地”。
“爸爸的小店掙不了多少錢,奶奶93歲了,大爺叔叔們輪流照顧。”劉文文坐在板凳上,輕聲說著。
2020年,在他初一的那段日子里,父母因感情不和結束了婚姻。父親劉金全排行老五,從小因小兒麻痹癥落下腿腳不便,只能守著這間小店維持生計;母親則在疫情期間遠赴浙江義烏打工,日子過得并不輕松。

“媽媽再婚又離婚,卻從沒斷過我的生活費,每個月1000元到2000元準時到賬。”劉文文記得清清楚楚,得知他考上大學,母親特意湊了5000元學費,還買了新手機讓他帶到學校,“她說在外打工再難,也得供我讀書。”
這份來自父母的愛,成了劉文文成長路上最暖的光。在灌南惠澤高級中學的課堂上,他永遠是坐得最直、聽得最專注的那個。成績單上,數學118分、物理90分的高分凸顯理科優勢,但75分的化學成績讓他總念叨:“這科沒考好。”
談及學習方法,他靦腆一笑:“上課跟著老師節奏走,課后再找練習補薄弱處。”沒有補習班,沒有優越環境,他就在書桌前一筆一劃寫、一道題一道題啃,“爸媽都不容易,我得靠自己。”
今年夏天,劉文文582分考取揚州大學。盡管專業被調劑到車輛工程,這個從小在生活里“闖關”的少年卻格外珍視這份禮物。“拿到通知書那天,我偷偷紅了眼眶。”他坦言,生活的拮據沒消磨志氣,反而讓他更早懂得努力的意義。
9月6日就要踏上去揚州的報到路,劉文文對未來已有規劃。“我想轉去電氣自動化專業,聽說這個專業好就業,未來還想考研。”他望著小店門口的鄉間小路,眼神堅定,“專業調劑是暫時的,只要夠努力,總能靠近目標。”在這間承載著生活重量的小店里,少年的求學夢正迎著陽光,悄然生長。
嚴蘇宇546分考取江西理工大學
零售店收銀臺后的“智能建造”夢


夏日的上海零售店里,空氣黏濕悶熱。18歲的嚴蘇宇站在收銀臺后,熟練地掃碼、裝袋、收款。
在灌南縣堆溝港鎮劉集村,一條蜿蜒的村路通往老屋,門檻被歲月磨得發亮。這是一個被生活拉扯著的家。不到1歲時,父母離異。他的童年被一分為二:在安徽阜陽,跟著外婆和母親生活,記憶里是母親在裝修公司早出晚歸的背影;小學六年級,他回到灌南,與年邁的爺爺奶奶相依,父親四處輾轉江蘇各個城市的工地打工,年收入僅一萬五千元,是這個家的經濟支柱。
高中三年,在灌南高級中學的教室里,他把自己“釘”在了書桌前。沒有琳瑯滿目的課外輔導書,但他有錯題本上密密麻麻的筆記;沒有昂貴的學習設備,但他有不肯向難題低頭的倔強。知識,是他唯一能緊緊抓住、改變命運的繩索。
今年高考,他為這個漂泊分散的家帶來了最堅實的光亮——以546分的成績,被江西理工大學智能建造專業錄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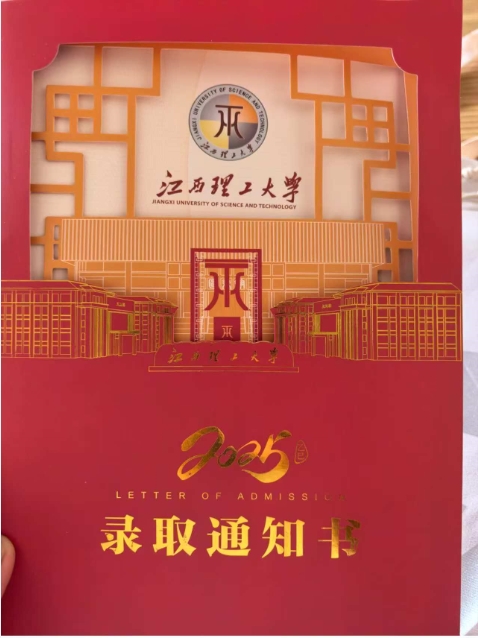
他選擇的智能建造,是一個用科技與智慧重塑建筑行業的前沿領域。對于嚴蘇宇而言,這個選擇包含著更為具體和溫熱的意義——他來自一個被距離隔開的家,他見過母親在裝修公司的辛勞,也深知父親在工地上的風吹日曬。他夢想著,通過學習先進的建造技術,未來能讓建筑過程更高效、更安全,讓更多勞動者能在更好的環境中工作。
喜悅之后,是學費的壓力。這個暑假,他投奔了在上海送外賣的舅舅,但沒有選擇風吹日曬的外賣行業,而是在一家零售店找到收銀員的工作。每天下午開始上班,一直工作到凌晨一點。
從阜陽到灌南,從灌南到上海,再從上海到江西理工大學,嚴蘇宇的足跡連成一條曲折卻始終向上的曲線。
生活給予他離散與粗糲,他卻用深夜的堅守,將每一張零錢數對,將每一個單詞牢記,將苦難熔煉成攀登的階梯。收銀臺后的深夜,不僅承載著他的學費,更托舉著一個未來工程師最踏實、最閃亮的夢想——用智慧建造溫暖,用技術凝聚家園。
患病父親含辛茹苦撫養長大
周小洲專升本圓夢心儀大學

灌南縣田樓鎮三興九組的鄉間小路上,三間瓦房靜靜立在玉米地旁。屋檐下的雜草剛被割過,露出些許泥土——聽說助學團隊要來,68歲的周良崗撐著腰,慢慢把門口收拾出一塊能落腳的地方。“一到下雨天,這兒全是爛泥,沒法走。”他拍了拍胸口,眉頭皺成一團,“老毛病又犯了,掛水消炎也只能頂一陣,查了有病,也沒錢治。”

屋里悶熱得很,墻角堆著些舊物,隱約飄著霉味。院子門口的鴨群“嘎嘎”叫著,周小洲站在一旁,寸頭利落,眼神卻帶著股韌勁。這個2003年出生的女孩剛經歷了人生的重要轉折——專升本考上了重慶師范大學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。“要選就選最好的專業。”她說這話時,語氣里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。
誰能想到,這個一心想讀好書的姑娘,人生早已刻滿坎坷。“沒見過媽媽,從小就跟著爸爸過。”周小洲說話間低了低頭,聲音輕了些,“我剛上大一那年,小一歲的弟弟在河邊玩,不小心溺水走了……”
大專三年,周小洲在重慶三峽醫藥高等專科學校的日子過得緊巴巴。“學費靠助學貸款,生活費全靠表哥堂哥湊,每個月給幾百塊。”她說,“在學校打掃宿舍樓樓道衛生,勤工儉學一個月能賺800塊,省著點花,夠吃飯就行。”原本沒想過專升本的她,是被同學拉著報了名,“大一時覺得能念完大專就不錯了,同學喊我一起,突然就想再拼一把。”
一旁的周良崗咳了幾聲,瘦得脫形的身子晃了晃。“我這身體,胃不好,腰也不好,干不了重活,全家靠低保過日子。”他望著女兒,眼里滿是愧疚,“她大姑去南京帶孫子了,以前還能偶爾幫襯點,現在也顧不上。暑假小洲去灌云她大姐家了,在那兒能省點生活費。”
大專三年靠著一股韌勁熬過來,周小洲的本科夢卻卡在了學費上。“9月5號開學,學費要5000元。”她算起這筆賬,手指無意識地蜷縮起來,“專科三年貸的款還沒還,本科學費又得想辦法。”在學校時,她總說“未來走一步看一步”,可真到了眼前,還是忍不住犯愁。
屋檐下的玉米葉被風吹得沙沙響,周小洲眼里重新亮起光:“總會有辦法的。大專三年都過來了,這兩年本科,我能勤工儉學,能再貸款,一定能讀完。”
●鄭惠文大一開學費用:7000元
●劉文文大一開學費用:6914元
●嚴蘇宇大一開學費用:6520元
●周小洲大一開學費用:5000元
總值班: 曹銀生 編輯: 賈元元
來源: 連云港發布
